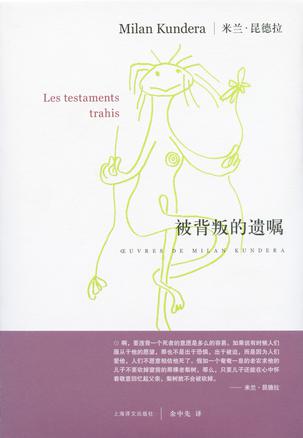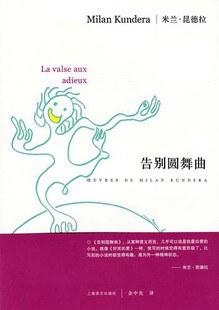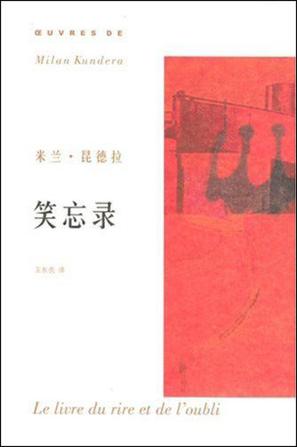依我看来,伟大的作品只能诞生于他们所属艺术的历史中,同时参与这个历史。只有在历史中,人们才能抓住什么是新的,什么是重复的,什么是发明,什么是模仿。换言之,只有在历史中,一部作品才能作为人们得以甄别并珍重的价值而存在。对于艺术来说,我认为没有什么比坠落在它的历史之外更可怕的了,因为它必定是坠落在再也发现不了关学价值的混沌之中。 对我来说,成为小说家不仅仅是在实践某一种文学体裁;这也是一种态度,一种睿智,一种立场;一种排除了任何同化于某种政治、某种宗教、某种意识形态、某种伦理道德、某个集体的立场;一种有意识的、固执的、狂怒的不同化,不是作为逃逸或被动,而是作为抵抗、反叛、挑战。
被背叛的遗嘱最新章节
作者的作品
好书推荐

快穿之不是炮灰的炮灰
似水年华流 为了委托人的愿望,也为了完成自己的愿望,女主在不同的世界穿梭。 另外本…

偷吻
时星草 阮萤因意外短暂失明,住进医院。进医院后,她听到最多的,是病人们对陆遇…

峨眉祖师
油炸咸鱼 岁月中,云岩上,李辟尘与一个白袍的童儿面对相坐。 仙山之中静悄悄,四只…

农家仙犬
钓鱼1哥 一个乡村三无青年,无房无钱无婆娘。 一只神奇三有小狗,大爱大福大仙缘。…

假绿茶她露馅了
姜沉漾 1. 裴季吟打游戏的时候碰到了一个绿茶妹妹。 妹妹声音娇软,撒娇苏到人的骨…

恶灵附身
剑上独觉 噩梦边缘,地狱重生。 当你经历一次午夜梦回,突然醒来,就会发现自己进入…

一击即中
抹茶丸子 人狠话少痞帅狙击手x人美毒舌医生小姐姐 - 曲筱阳相过一次相亲,恶梦一般。…

想你时心稀巴烂
舒虞 传闻陆南渡玩世不恭,直到某天酒吧来了个女人,陆南渡看到她下意识摘下唇…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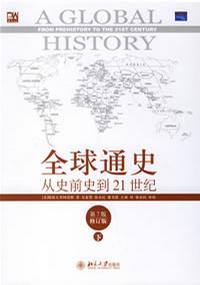
全球通史(下):从史前史到21世纪
斯塔夫里阿本书分八个部分,四十四个章节,主要讲述了世界历史的进化,世界文明的发展…

刹那星光
明月珰 暗恋是一种病,得治。 裴少:曾经有一段真挚的暗恋摆在我面前,我没有珍惜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