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一部 第十七章 潘帕斯大草原(第2/4页)
“栏舍”不远处有个坑,坑里还留有灰烬。“栏舍”里还有一张凳子、一张破牛皮床、一口锅、一条铁链子、一把煮“麻茶”的壶。“麻茶”是南美人常喝的饮料,印第安人的茶。“麻茶”是一种熔干的叶子泡的水,用麦梗子吸的,和美洲人喝其他饮料一样。应巴加内尔的要求,塔卡夫煮了几杯“麻茶”,大家边吃干粮边喝茶,爽极了,都说这茶味道不错。
第二天,10月30日,红日东升,热雾腾腾。这一天骄阳似火,暑气蒸人,平原上连个可避荫的地方也没有。然而,大家依然无所畏惧,顶着烈日继续向东进发。他们多次遇上一个个庞大的牧群,牛羊在盛暑之下静静地躺着,连吃草的力气也没有。放牧的人连个人影儿也不见,只有几只狗守护着那大群的牛羊,这些狗口渴时惯于吸羊奶解渴。这里的牛都很温驯,不像欧洲的牛,见了红色就惊惧乱跑。
“它门不怕红色,想必吃的是共和国的草(2)啊!”巴加内尔说,他这句话虽然太法国式一点,但也还风趣。
午后,草原上的景物发生了变化,由于大家的眼睛看厌了单调乏味的东西,一见有点变化就兴奋起来了。禾本草类开始越来越少,牛蒡子越来越多,还有驴子爱吃的八九英尺高的大白术,矮小的少纳尔树和墨绿色多刺的小树四处都有,稀疏零落,这些都是干燥土壤上容易生长的植物。这之前,平原上的黏土依然湿润,所以牧草长得茂密丰厚,宛如地毯。现在这“地毯”开始变旧,大块的毛都掉落下来,露出麻线底子——贫瘠的土地。这是地面越来越干燥的缘故。塔卡夫提醒大家,前面的路会更加艰险。
“我觉得变换下也好,”奥斯丁说,“总是青草,我的头都看大了。”
“是呀,但是,有草,才有水喝呀。”少校回答。
“啊!水不用愁,路上总会遇上小河。”
这番话如果让巴加内尔听见了,他一定会说,在科罗拉多河与阿根廷行省的山峦中,河流极少。但,此刻巴加内尔正和哥尼纳凡说话,后者要他解释一下眼前的奇特现象。
原来,他们感到了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烟味,而四周却连个火星也没有。也没有看见哪儿失火冒烟,那么,这股烟味又从何而来呢?一会儿烟味变得越来越浓。除了巴加内尔和塔卡夫外,没有一个人不感到惊讶。那地理学家似乎是个万事通,任何现象他都能解释,此刻,旅伴们正洗耳恭听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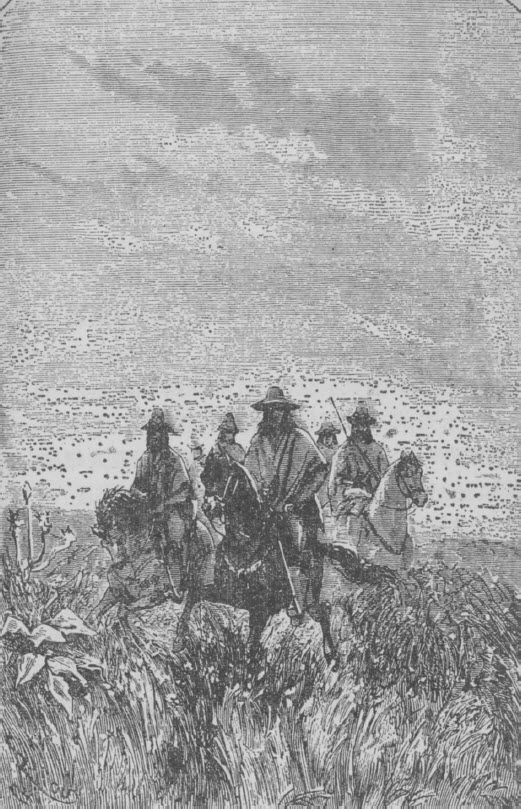
马儿在草丛中大踏步地前进
“我们看不见火却闻到烟味,按常理,‘无火不成烟’,这话不论在欧洲还是在美洲,都是一个理儿。所以,附近某个地方一定有火。只是潘帕斯平原广阔无垠,气流畅通无阻,常常在七八十英里以外烧草,都能闻到气味。”
“七八十英里以外?”少校表示怀疑。
“可不是吗?”巴加内尔肯定地说。“不过,还得补充一句,火是在大规模燃烧的情况下,往往是烧到了一个极大的范围了。”
“那是谁在草原上放火呢?”罗伯特问。
“有时是打雷引起的;有时可能是草晒干了,印第安人放火烧的。”
“放火烧它干什么?”
“他们认为——这种观点究竟有什么根据,我可不知道,他们认为草原上烧过后,草会长得茂盛些。若真是如此,应该就是他们想用草木灰来作肥料。不过,我倒认为,火烧草原的目的是灭虫,有一种寄生虫,名为“兽虱”,对牲兽危害极大。只有放火,才能把千千万万的兽虱烧死。”
“不过,这么一来,岂不是城门失火,殃及池鱼,草原上的牲口也因此而断送了性命吗?”少校问道。
“是呀,有时是烧死不少。不过,这儿牛羊太多,烧死一点,又算什么呢?”
“我担心的倒不是牛羊,”麦克纳布斯少校说,“我是在为穿过这草原的旅行者们发愁,万一遇上大火把他们包围起来了,该如何是好?”
“唉!这有什么好怕的!”巴加内尔叫起来,一副满不在意的样子,“要真遇上这事,那才好呢,难得一见,可以大饱眼福。我倒不在意。”
“瞧,这就是我们的学者,他研究学问非要一直研究到被活活烧死为止。”哥尼纳凡说。
“鬼晓得,我亲爱的爵士,我才不会那么傻。我读过美国小说家库柏的游记,主人公皮袜子曾告诉我们:若遇上了野火,把自己四周的草拔掉,拔出一块直径数米的空地,就可以避开火势。这办法很简单。所以我不担心火烧过来,反倒希望能看到一场大火来临。”
巴加内尔希望观赏一场弥天大火的愿望没有实现。但他现在已经被烧到半焦了,烈火一般的阳光倾注大地,把旅行者们炙烤得无可奈何。在这样热的气候里,连马也喘息不停。除非偶然飞来一片浮云遮住火球,否则见不到半点荫凉之地。即使有一片阴影在平地上流动,那骑马的人都会快马加鞭追着那被西风吹到他们前面的云影,但马总跑不过云彩,转眼间,赤裸的太阳又露出云层,洒下一片“火雨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