莫道不销魂说李易安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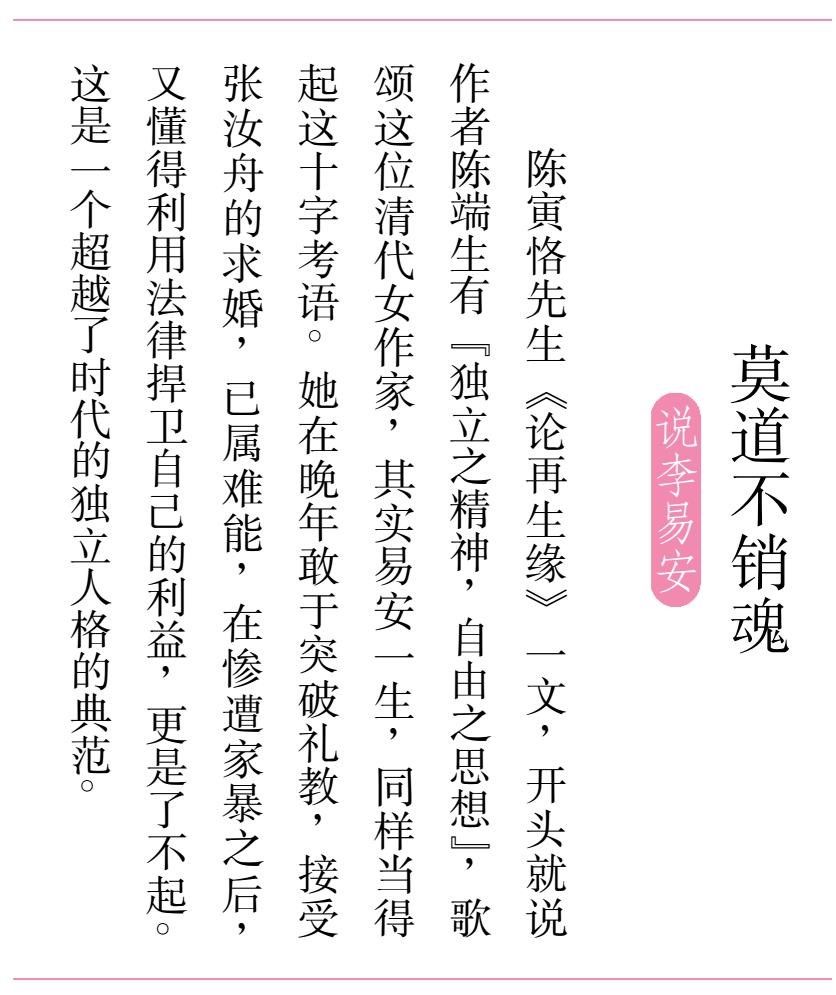

文学的本质是人学,丹麦学者勃兰兑斯在他的不朽名著《十九世纪文学主流》一书中说:“文学史,就其最深层的意义来说,是一种心理学,研究人的灵魂,是灵魂的历史。”所以,我们在阅读一位作家的作品之时,除了要了解他的生平出处、社会背景,更需要用心去倾听作品背后无声的呼告呻吟,剖析作家的心理症候,感受他或她的灵魂悸动,这样才算是一位合格的读者。历来对女词人李清照的研究,多侧重她的身世与词风,却甚少涉及对其性格底色的深层探讨,这无疑是非常大的缺憾。
李清照,字易安,号漱玉,山东章丘人。父李格非,字文叔,是北宋著名的文士,为文高雅条畅有义味,与苏门诸人关系密切,后亦名登元祐 党人碑;母亲王氏,是状元王拱辰孙女。家中浓郁的文化氛围,让易安自幼即徜徉书海,才堪咏絮。元符二年(1099),易安年十八,时为礼部员外郎的父亲把她嫁给吏部侍郎赵挺之的季子,太学生赵明诚。这头婚事在当时可算得门当户对,但徽宗朝赵挺之做了宰相,打压旧党,不遗余力,李格非却因身沦党籍,遭到政治迫害,两家的裂痕越来越大。赵挺之任相职后,易安曾献诗几谏(对长辈委婉而和气的劝告谓之几谏) ,有“ 炙手可热心可寒”之语,父李格非遭到迫害后,又给公公上书请救,想以“ 人间父子情” 打动赵挺之,不过,这些对热中权势的赵挺之而言都是徒劳。
易安与赵明诚的婚姻,长期被视作鳒 鲽相依的典范。元朝伊世珍《琅嬛 记》编造了一个著名的故事:
赵 明诚幼时 ,其父 将为择妇 。明诚昼寝 ,梦诵 一书,觉来 唯忆三 句云:“言与司 合,安上 已脱 ,芝芙草拔 。” 以告 其父 ,其父为解曰 :“汝待得能文 词妇 也。‘ 言与司 合’ 是‘ 词’ 字,‘ 安上 已脱’ 是‘ 女’ 字,‘ 芝芙草拔’ ,是‘ 之夫’ 二 字,非谓汝为 词女之夫乎? ” 后李 翁以 女女之,即易安 也,果有文章 。
宋以后,易安词名藉甚,故《琅嬛 记》所载的故事虽然荒诞不经,而词女之说,久已深入人心。人们想到了易安,首先想到的一定是“ 女词人” 这个标签。易安的生理性别造就了她在文学史上的地位,但也局限了人们对她的进一步认知。
杨海明先生说:“李清照之所以受到当时和后世男性文人的赞誉,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沾了她女性身份的光。”(《唐宋词与人生》) 我非常认同这一见解。清代常州词派的理论家周济就认为“ 闺阁词唯清照最优,究苦无骨”,我的太老师朱庸斋先生赞襄兹说,他在《分春馆词话》卷五中说:“历来对清照词作之评,往往偏高溢美。其词清新流丽,自然中见曲折,然生活面狭隘,闺阁气重,不免近乎纤弱。……后世不少柔靡轻巧之作,与清照流风不无关系。”我们知道,中国文艺的审美旨趣,固然重视阴阳相生相济,但仍是以乾动阳刚为主,易安的词缺乏风骨、偏于柔靡,自风格体性言,是纯然的女性词,固然在当时独树一帜,然而衡诸中国文艺的主流,确实离名家、大家的标准差别辽远。
易安在词坛的地位,是经后世文人的过分推崇而逐渐形成的。不过,宋代对易安的褒评都是基于她的诗文,而非她的曲子词。如胡仔云:“近时妇人,能文词如李易安者,颇多佳句。”这里的文词是“诗古文辞” 的“ 文辞”,指古文、骈文、赋,不是指曲子词。又引《诗说隽永》说:“今代妇人能诗者,前有曾夫人魏,后有易安李。”南宋理学家朱熹云:“本朝妇人能文,只有李易安与魏夫人。李有诗,大略云‘两汉本继绍,新室如赘疣。所以嵇中散,至死薄殷周’云云。中散非汤、武得国,引之以比王莽。如此等语,岂女子所能?” (《朱子语类》卷一百四十) 他认为,宋代妇人能文的,只有魏夫人( 其丈夫是曾为宰相的曾布 ) 和李易安,但易安除了文章之外,还能诗,且写得不赖。他举的例子是“两汉本继绍,新室如赘疣。所以嵇中散,至死薄殷周”。“嵇中散” 是嵇康,他是魏晋时“ 非汤武而薄周孔”“ 越名教而任自然” 的名士,后为司马氏所杀。嵇康表面上毁弃礼教,实则是真信仰礼教,因为不满司马氏篡权,利用和亵渎礼教,这才非薄汤武革命,以商汤代夏武王伐纣为臣弑其君,挑战儒家传统观念。易安这几句诗的意思是,东汉继承西汉的法统,是政权的合法延续,中间王莽篡汉建立新朝,只是像人皮肤上长了瘊子,不能改变历史正统,嵇康非薄殷商代夏、周朝代商,正因坚持了历史正统观的缘故。易安身亲离乱,其时宋室君臣因靖康之难被掳北上,金人在北方扶植刘豫建立起伪齐政权,易安此诗,或即为此而发。古代女性由于所受教育及参与社会生活的限制,一般来说,诗文不像男性那样綦重家国情怀,易安诗却绝非闺阁之秀,直是文士之豪,这也就难怪朱熹感叹:“如此等语,岂女子所能?”